---------关于文化误读的话题
讨论人员:张颖川、熊宇、张发志

张发志: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逐渐升温,这既是大的趋势,也是必然。但是,当我们重温传统的时候,却发现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看不懂文言文了,这几乎是繁体汉字定格以后,在传统文人那里从未有过的事,于是,当我们再拿起文言文的时候,就必然要借助于解释,虽然,古人读书也借助于“注”“疏”等,但其中的差距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今天也许连一些常识也可能会弄错。比如,我最近看的牟世金版《文心雕龙》就发现有很大问题。我当时有个很强烈的感受是,这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实际上并不是很深。
张颖川:作者可能是40年代以前出生的吧?
张发志:牟世金这个人我并不了解,后来还查了下他的简历,他28年出生,89年去世,也就说他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应该是在50年代,而那个年代恰恰是政治领衔的年代。那时的学者,普遍的一个问题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判中国过去的传统,当然,我现在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那时会把唯物主义定义为正确的,而把唯心主义定义为错误甚至是反动的。因为,对我来说,无论什么主义都只是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一种角度而已。重要的是你的解释是否符合作者本来的意思,当然,也许,就在我们试图去还原作者本来意思的时候,误读就已经产生了,但这和用一种认识方式去评判原著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看一本古代文献的时候,最重要的态度是,你不仅要跟着那种上下文关系和思路去理解这个字,还要理解同一个字在其他文献中是什么意思,如此,也许才能相对准确的把握住他本来的含意。如果直接就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对这个东西进行评判,不但批评毫无价值,就连赞扬也毫无意义。联系这个思路我们来看西方的翻译书的时候,也会发现这种问题,没有办法,当你自己不能很专业的理解原文的时候,你就会受到翻译家的影响。比如我们随便说个“静物”这个词:“静物”这个词英文原文是still life, 直译是“寂静的生命”或“永恒的生命”的意思。
张颖川:我还真的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中文的“静物”一词在西方英语中的表述是“still life”,美术界的“静物”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国内美术界一直都是这样翻释的吗?
张发志:对,一直都是用的这个,但是我们国家的翻译是“静物”,着重点在“物”上面。
熊宇:确实是这样,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翻译西方著作时会遇见一些词是没有办法用汉语和英语直接对应的,这样一来本身两种语言互译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歧义,比如张发志刚才举那个“静物”的例子,就很典型。不管是看文字作品还是视觉的作品,一定要尽量回到作品当时的语境,特别是艺术史上的重要作品,一定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创作者的时代背景,才能感受到作品真正的意义。如果抛开环境和历史语境来阅读作品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会被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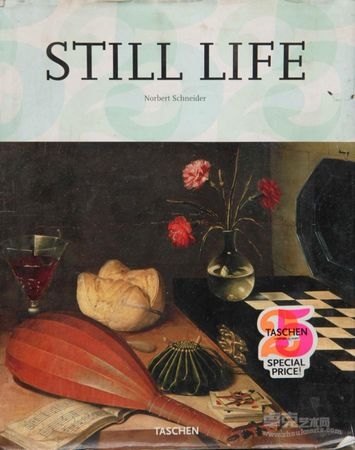
张发志:是的,对于一个懂英文的人来说,still 有“不动的,寂静的意思,也有仍然,持续的意思,life是”生命,生”的意思,总之,无论怎样,也没有“物”的意思。”永恒的生命”或“寂静的生命”的文化背景更多是在“精神”层面,而“静物”这个词是“物”的概念,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从这里出发,我们再来理解西方历史上的“静物画的时候”,我相信,体验就大不相同了。
熊宇:而且不同的国家民族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各不相同,各有区别,这种区别造成每个民族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都有其语言背景。其实文化并没有说某种文化就一定比另一种文化优秀,但如果站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立场上,不看别人的历史文化背景,那绝对会有很多误读会产生很多的歧义,这些歧义多年不修正就会流传下去,很多年后人们甚至会发现这种歧义变得理所当然。今天我们和西方文化机构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在阅读我们的艺术作品时,同样也会误读。很多时候他们也是站在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上来阅读我们。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展览,或一个学术讨论之前,应该先做一个学术背景的介绍。比如今天我们谈论某件作品或一个话题,我们自己当然会有一个专业知识背景方面的上下文,自己自动就会对其有个简单的注释。但其他的人没有进入过这样的语境,就会觉得理解起来会有障碍,而当人在理解上遇到障碍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在自己以往的经验记忆里面去寻找理解的基础,而这正是文化误读的源头。
张颖川:你们两人今天谈论的话题比较深刻啊,涉及到诸多方面:首先一个方面是我们今天阅读自己本土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时遇到的语言文本交流的实际问题。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我们传统艺术理论的一座高峰,历经一千多年,无人翻越它。你们川大中文系有一名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被尊称为国内“龙学”泰斗。他1958年出版了首部专著《文心雕龙校注》,这本书当时在海内外包括日本在内的学术界中获得很高的声誉,至今都定位为《文心雕龙》现代最好的校注版本。我没有这个研究方向,也没有像张发志那样仔细阅读的体验。不过我和你们不是一代人,我是50年代出生的,高校77级的中文系毕业生,阅读古代典籍,除了一些看不懂的“字”“词”需要翻阅注释外,一般都不看释文,尽可能通过自己反复阅读原文理解。当然这和我家里有一个汉语言史的教授有关,但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好多上个世纪特别是60年代后出版的古籍注释文带了较多的当年文化革新痕迹,张发志手中那本《文心雕龙》校注书是80年代出版的,与杨明照先生30年代研究50年代出版的可能会不一样,没有看过那本书,具体的不敢妄评。不过从中引发思考一个今天我们都要面对的事实: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大革命热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国内知识分子为寻求民族振兴富国强盛的道路,以西方文明为进步标准,满腔热情地革新民族传统文化,从各个领域全面改造本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这种改造学习的方式基本上是尽可能地加快速度和“拿来主义”式的,当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倡导白话文,撰写《白话文学史》,那一代人就推翻了二千多年历史的文言文,由此造成我们这些不懂文言文的后代看自己民族的经典书十分吃力,不得不借助释文,而释文自身有时代烙印,带有这个语言文本当时当地现场语境表述特点。当年我们读书时,老师就在提醒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大革命时代的古籍“注解”释文,不同时代的相互“差异”和“误读”是必然的。

成都抗日时期创办的《战时后方画刊》12-13期封面
“约定俗成”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语言文字的表述形式和对历史的理解阐述方式随时尚生活时代文化精神交流的实际要求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身处于不同时代生活中的人的文化精神及随之发生的交流习俗在不断发生变化,我曾经编修撰写过《成都美术志》,查阅了好多20世纪史料,《成都美术志》还专门设立了“教育”一章。记录了本土早期美术教育现状。
熊宇:《成都美术志》我没看过,但早期美术教育的问题很有意思。
张颖川:上个世纪初兴起的国内学校美术教育体系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辛亥革命后,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他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彻底革新传统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对国内现代美术发展最有影响的是美感教育。 蔡元培先后进行“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文章,并于1918年在北京支持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到30年代,全国各地的美术专门学校,艺术专门学校就已经有几十个了,其中担任主要教学的老师一般都是从西方留学回来,或者是到上海、北京学习的毕业生。比如我们四川美术专门学校老师,多数是从上海回来的毕业生,他们在教学中都把西画的素描、色彩和写生等作为学校新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力推广。显然,这些在现代“美育”精神指导下兴办的学校美术教育一开始就带有改旧换新的社会革命参与热情和干预责任。我在《成都美术志》中专门收录了这样一段史料:1921年12月,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专修科师生与该校其他部的教员、学生成立“美术学会”。这是成都最早的美术社团,成立大会在成都高师圣公堂举行,会场气氛异常庄严,大会仪式严肃,首先乐器演奏,然后成员唱国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会长杨伯钦在演说中说:“现在我们组织这会要有改造的作用,一方面使一般人养成美的观念及美的环境,我们每年可开次展览会,拿一般人的审美渐次唤醒起来,那么中国就有进化的一天了。”上世纪初的美术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活动很多都是学校美术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的展览会和写生活动。我不懂翻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把“still life”翻译为“静物”的。如果把“静物”这个词放到当年的中国社会实际现状中,放到当时当地美术活动的文化背景里,可能可以理解那个“物”的意思。一大片被西方列强打得衰败不堪四分五裂的国土,国民关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很高。那一时期的中国需要工业,需要铁路、需要钢筋水泥铸造的桥梁,还渴望飞机、大炮等,甚至包括最基本的“吃饱饭”的愿望。20世纪初以西画画理为主的新学校美术教育对于清未文人书房中沉浸于笔墨韵戏的中国画坛来说,对于具有“天人合一”“似与不似”“形神兼备”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肯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重新开启重新看待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觉艺术大革命。美育开放了人的审美感性感想,西画的色彩与造型在当时的中国画家看来,比传统山水画、花鸟画更能接近自然物质的真实世界,更方便于描写自己个人眼睛所看到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物,由此抒发由现实场景产生的人的真情实感也更加直接有力。当然这么快速发展的美术学校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有“粗糙”。20世纪国内各种革命运动、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一个接一个,一浪高一浪,一波接一波,而一开始就以宣传启蒙社会革新为功利责任的中国现代新美术,始终处于各历史时期革命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表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潮成为革命美术的主流。到1949年后,美术界全盘学习苏派,美术活动以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正是我们中国社会革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50年代至70年代的主流画种还有年画、连环画、漫画,这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社会宣传效果又快又好的绘画形式长期受到新中国党和人民政府文艺政策的扶持和推广。记得我刚到画院跟胡仁樵老师学素描时,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说,苏联契斯恰柯夫的素描体系讲究块面结构,一般人容易掌握,好学。
熊宇:但是张老师,根据我们自己多年学院素描绘画的深刻体验,其实苏联契斯恰柯夫的素描体系并不容易掌握。
张颖川:真的啊,又是差异的误读。当时在我们的头脑中,感觉凡苏派的就有无产阶级人民艺术精神,而人民性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学习掌握上就不应该太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艺术理论概念是直接从苏联拿过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原则基础写的《生活与美学》一书,在“文革”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学院艺术理论课的必读经典,我阅读这本书就感觉通俗易懂。
熊宇: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一个事,比如谈到民国时代学院的建设,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当时建个学校,学校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它的教学核心其实是按照我们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来建立的,就是说这种体系的建立本身就存在有一个文化间的隔阂,会有一个误读。

战时后方画刊6期-梁正宇木刻《寒衣》-
张颖川:你说得有道理,我一直认为民国初年到国外学习西方美术的人不少,而那一时期现实主义并不是西方美术的主流,但国内最终以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为主流,而不是刘海粟、林风眠等人的艺术主张,这是中国本土自身历史的原因,与艺术家个人没有关系。贫穷落后的中国人需求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精神,需要科学技术。当年胡适关心中国之急需的适用主义思想很有影响。
张发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自己的文化丢了,学西方,又是只捡自己“需要的”学习,也许“不需要的”才是西方文化的精髓,现在看来,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付出代价了。
熊宇:在当时看来科学这个东西才是符合我们时代需要的。
张发志:那时,对科学的认知更多是指科学技术,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从社会学的层面,科学有客观的看待事物发展规律,并且做出系统的,有理有据的研究的意思,里面包含有尊重的意味。而那时,他们提出“全盘西化”显然就不那么科学了。所以,他们那时理解的科学,其实也是一种误读。
熊宇:前段时间看微信订阅号设计号,其中有一条是“最受国际认同的几十个中国图像”,你就会发现这个图像非常符号化,比如石头狮子,比如旗袍等。你会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文化图示代表中国。

网络上具有强烈中国元素色彩的图片
张发志:是的,你看《功夫熊猫》比中国拍得还中国。
熊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论语》《四书五经》有自己的美学思路,只是说这种美学和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并不一样,不是一种表象,不是画面的绚丽,而是一种背后思维的美学,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而这种非常中国的感觉西方人就不是很了解。我曾经遇到一个例子,我们美术馆来了一个荷兰的策展人,他初次来到中国,到我们这里看展览。当时有很多画,有一件我记得是传统水墨画的荷花。我们当时问他感觉如何,我也想知道一个当代艺术的西方策展人如何看待这样的中国传统作品。他就说作品如果有强烈的情绪会更好,接着就举到了梵高的例子。我就感觉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大了解,后来给他解释了作品的背景,他听了之后很快就理解了。那次看展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一个有文化背景的人往往是从他的文化角度和知识结构来理解和解读这个作品,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带偏见,而是因为他确实不懂背后的故事。今天比如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艺术机构解读中国的艺术品,很多时候会发现他们是带着他们的知识结构来看我们,如同我们看他们一样。

电影《功夫熊猫2》充满中国元素和好莱坞风格
张颖川:除了要面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历史变迁,面对今天的文化与昨天以至两千来的传统文化的差异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很喜欢西方一个哲学家,哈贝马斯,他被世界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有一个“交往理论”很受欢迎,注重以语言为中介的没有强制权力的交流互动,这个交往互动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承认差异,包括各个专门系统的差异,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张发志:这是很理想的观点,个人要做到相对容易,但要求一种在经济和政治推动下的强势文化保持谦逊就太难了。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张颖川:如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中受到了热烈关注,就表明当下世界强势文化话语霸权正在遭遇挑战,人的个体个性本真自觉诉求正在获得尊重,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多元化现象正在得到关注。所有理论思想创造性提出的动力都来自于人的现实生活存在的需求,虽然是相对意义概念,但有实际实践价值。认同当今多元化个性化的差异与误读,自然就可能接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社会互动交往行为的呼吁需求。正如我们现在能够心平气地议论《文心雕龙》版本的释文话题,熊宇愿意向荷兰策展人细心解说中国的传统水墨画,对方也在认真倾听和理解,这样在差异背景下的互动交流都是真实积极有效的。

左:盛邦 张颖川 熊宇 张发志
文章首次发表与《1314》杂志第36期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