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唐代工笔仕女画生态因子和绘画因素的追溯
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生态因子和中国绘画的产生是同步的。
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论述中国绘画的产生时,从中国文字的产生谈起:“人类表达意义之工具有三:一为姿势,二为语言,三为文字。文字之发展,实分三阶级:一曰结绳,二曰图画,三曰书契。……参观柳诒征著《中国文化史》及蒋善国著《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庖牺作八卦为文字之始,其仰观俯察,为宇宙万物之抽象表现,巳具备后世绘画写生之方法。……《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竹书纪年》:‘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观此可知传说已久,及后纬书盛行,更多敷会。大抵上古之人,观龟背之纹,鱼龙之形,有所悟而作图画,遂故神其说以惊世。……《世本》:‘史皇作图’,宋忠曰:‘史皇黄帝臣,图,为画物象’。是知中国之文字与绘画无不发源于描写自然界之物象。[1]
在谈到中国画色彩起源时,俞先生说:“原始民族之雕题文身,所以畏敌求偶,乃后世装饰艺术之发源。后以气候关系,不得不着衣服,遂有染画衣服之制。如黄帝虞舜已有此风,至今未改。……《通鉴外纪》:‘黄帝作冕旒,正衣裳,视晕翟草木之华,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安国云:‘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2] ”。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绘画通史》中说:“《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土似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虽然这是作为定‘仪礼’、‘伦常’之用,但也透露了这个时期对于色彩的识别与处理”。[3]
俞剑华先生还谈到了传说中最早的画家是位女性:“舜妹嫘首遂有画祖之号,……金赍《画史会要》:‘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4] 虽然从史料中未发现其画迹的记载,但推想其作画时,对女性形象的表现亦当有所侧重。
[1]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第2—5页,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初版
[2] 见同上
[3]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52、53页
[4] 同注1
俞先生对这一段论述总结时说:“以上乃史前时代,传说之大略,其可征信之程度,殊为微弱,不过绘画随生民以俱来,时至唐虞,汉族文化已灿然可观,绘画必巳发展至某种程度,固可推想及之也”。[1]
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绘画因素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工艺。“制陶工艺是新石器时期最突出最丰富的美术创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2]著名考古学家邵望平先生更是说:“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及人形附饰,陶寺的彩绘艺术与乐器,大汶口—龙山文化优美的陶器造型和玉雕、牙雕,北方赵宝沟类型陶器的动物形纹饰,红山文化的塑像、动物形玉雕,新开流渔猎文化的骨雕,大溪—屈家岭文化的白陶半浮雕式纹饰、薄胎彩陶、晕染彩陶,湖北龙山文化的陶塑动物,河姆渡文化的骨、角、牙雕,良渚文化陶器上的精致的蟠螭刻纹和以琮、钺为代表的玉雕艺术等等,使中华史前艺术领域流光溢彩、绚丽多姿。这些成就成为其后文明时代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的直接源泉[3] ”。这段话点明了彩陶艺术是文明时代艺术成就的渊源之一,对以后时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色彩的运用,是在线条运用基础上审美领域的开拓,可以视为重彩工笔仕女画“彩”的萌芽。

图4.1 《舞蹈纹彩陶盆》
对于施用“彩” 的工具——笔的情况,李福顺《中国美术史》中谈到仰韶文化陶器的制陶工艺和特点时有这样的论述:“彩绘工具可能是原始毛笔或钝头工具。这是根据彩陶纹饰中的笔痕推断的,并未发现实物。彩绘颜料在不少原始文化遗址中发现,在半坡、姜寨及北首岭等地的墓葬中发现过盛有颜料的小罐和带有红色颜料的研磨用锤、磨石及石砚等。这大概是善制彩陶的能工巧匠的随葬品”。[4] 虽然没有具体笔的记载介绍,但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原始色彩的选用和制作方法之一是对天然矿物色的研磨。可以想象出,原始人一定是用笔一样的工具,用水或其他介质调合色彩使用的。
[1]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第2—5页,上海:上海书店(1937年)初版
[2] 见薄松年主编《中国美术史教程》第3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3] 邵望平:《史前艺术品的发现及史前艺术功能的演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上)第27页,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年
关于工笔仕女画的起源的最原始资料,我们可以从彩陶中得到信息:仰韶文化彩陶半坡类型的彩陶盆中,出现了人面和鱼结合的图像,这说明原始先民在观察和表现各种事物时把人物已经放在了一定的位置中;在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图4.1)上更是以女性化的人物为主体,简括的形象中突出了像女性辫子状的头饰物。由于马家窑文化属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些舞蹈者似乎应是女性。此画笔法简单,只是呈轮廓状,但简洁明朗的画像给我们探索工笔仕女画的起源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与雕塑中,人物形象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女性形象。这说明原始先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认识自身的能力也在逐步地进展着,如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其中有孕妇塑像(图4.2),腹部凸起,臀部肥大。辽宁省建平、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情。尽管红山文化的雕像表现了对祖先的崇拜或寄托对大地母神、对农业丰收及生殖的愿望,有着多方面的价值,但从对人、特别是对女性形象的观照,也说明了一定的性心理的存在与表现。[1] 这些性心理应视为对女性的绘画与雕塑形象的审美动因之一。

图4.2《陶塑裸妇》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原始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它以自然界的物像、人类自身、符号等作为描绘的对象,写实或抽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境界、观念意识和创作能力。彩陶作为我国最早的色彩画面,对后来的绘画艺术影响深远。
[1] “ 1905年,弗洛依德出版《性学三论》一书,他把生物发生原则用于研究心理性欲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做了种系发生的和个体发展的观察与概括。1914年,弗洛依德发现自恋的心理现象,并以先天的内部驱力,即爱力来解释人的行为,认为生命由此得以支持。这一能量称为生本能,其投注于外即为爱情的对象,投注于内即为自我爱恋。” 见《本能的冲动与成功.封二介绍》,弗洛伊德著,文良文化 编译, 华文出版社,2004年。这时期的彩陶作者有可能是女性,但更有可能是男性。一般男性作者对女性观照更为周全。
4.2 战国时期工笔仕女画的初步面貌
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受到更多的关注的基础上,在漫长的绘画发展过程中,工笔仕女画伴随着人物画的发展而发展。
殷商时期就有人物画的记载,“如《史记.殷本纪》(第三)提到,商朝初年,宰相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刘向《别录》说他还画了‘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等九主形象来劝戒成汤。又据《尚书》载,商朝的‘中兴’之主武丁,为了缓和奴隶的对抗,要用奴隶傅说做宰相,即位后,自称梦见圣人,名叫说,并画出说的形象,令百官到处去寻找,终于在奴隶中找着了。《尚书.商书.说命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尚宗武丁,‘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子良弼,其代子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1]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绘画是以人物画为主的。郑昶先生说:“研究我国人物画以夏、商、周三代为开始更具说服力:自三代至秦汉,绘画主要做为政教推行的工具,可称为礼教化时期;自三国魏晋迄於隋唐,绘画成为佛、道教的宣传,可称为宗教化时期;自五代历宋元明清以至今日,绘画纯粹作为审美欣赏,且与文学、书道结合一起,可称为文学化时期”。[2] 人物画的发展阶段大致是按此划分的,这样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唐代人物画的工笔仕女画,其绘画面貌也是按上述三期来逐渐成熟的,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工笔仕女画就已经按自身面貌独立发展了。
汉代刘向《说苑》中记述商纣王建鹿台,有“宫墙文画”;[3] 《孔子家语.观周》中也记有孔子观周明堂的壁画之事,上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具善恶之状”[4] 等。《淮南子.主术训》称:“文王、周公观得失,徧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着于明堂”。[5] 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宫殿壁画发展兴盛的主要动因。统治者的需要(包括宗教的推行)和社会生活需要,加之人物画自身具有的高超的技艺、传神的艺术感染力和展现的时代精神,既足以赏玩,又具文化历史价值,因而使得人物画绵延至今。从绘画本身来看,绘画自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被列入最高学府“鸿都门学”[6] 必修课后,画家和绘画的地位迅速提高,再经南北朝的发展。特别是帝王画家和文人画家出现,使得绘画从“游于艺”而为“与六籍同工,四时并运”[7] 了。唐代由于唐太宗武功文治兼备,因此建国后数次举行大规模的图绘功臣的活动和道教佛教绘画活动,刺激了绘画飞速发展,促成了以人物画为代表的绘画高峰的形成。
[1]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52、53页
[2] 参见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9年
[3] 汉·刘向《说苑》,见www.yjsy.ecnu.edu.cn
[4] 魏·王肃 注《孔子家语·观周十一》,见www.white-collar.net
[5] 汉·刘安《淮南子》(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影写北宋原本书,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6] (根据《东汉会要》卷十一《鸿都门学》改写。详见《后汉书·蔡邕传》和《阳球传》),转引自李福顺、吉淑芝遍《中国美术典故集粹》第332—334页,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年
[7] 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图4.3《人物龙凤图》
人物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是其他画种所不能相比的,人是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从艺术方面看,当人本身被当作关照与表现的对象时,更会被用来促进人对自身生命的自觉。有史以来,我国的人文思想就极为发达,人物画可以说是我国人文精神的代表画种,而工笔仕女画与工笔人物画自诞生之时就是密不可分的,同样是我国人文精神的代表画种,并且还有着自身怡情悦目的特点,某种意义上说,更富于直觉感悟的艺术观赏价值。
目前发现的最早和具较完备中国绘画工笔仕女画特征的是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图4.3),其主体人物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因此可以认为工笔仕女画是工笔人物画开端时期就有的绘画形式。[1] 秦汉时期卷轴或屏风形式的工笔仕女画目前尚未见到,但湖南马王堆汉墓帛画(图4.2)可视为初期面貌的工笔仕女画。汉魏故事中记载的妃后列女图,也应该是仕女画的初期面目。汉魏间妇女图像者甚多的宫庙壁画,和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所描绘“下及三后,媱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图像,也可以视为此时期工笔仕女画的早期绘画。关于图4.2帛画的内容可从屈原的《楚辞》来验证:[2]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唯魂 是索些。十日代山,流伞铄石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悉散而不可止些。……《楚辞·招魂》
[1] “真正独立的绘画作品是在湖南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出土的两幅画在丝织品上的图画”,见薄松年主编《中国美术史教程》,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2] 参考李泽厚《美的历程》118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汉代艺术家们在艺术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个登仙祝福、有神灵保护的神仙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苦难,只有欢乐愉快,这幅汉代帛画艺术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当时,连秦始皇、汉武帝都多次派人寻仙和求不死之药,那么所有的人们当然也是希求人生能够永恒延续的了。当时的观念认为,神仙世界不是难以企及,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就能够到达的,所以汉代有厚葬之风,在墓室中有着大量“祈福升仙”之作,把那个世界创造成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充满人间的乐趣、而又稚气天真的神的世界,希冀通过这种艺术象征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此,这幅用于“祈福升仙”帛画用工笔画的形式,浓墨重彩、铺陈式地画出繁杂的内容,体现着人们延续生命的自然本能要求,所描绘的天上、人间和地下一体的、“龙蛇九日,鸱鸟飞鸣,巨人托弧主仆虔诚”[1] 等内容,就是用画面表现出的《楚辞》等篇章中的想象奇异、绚烂瑰丽的远古神话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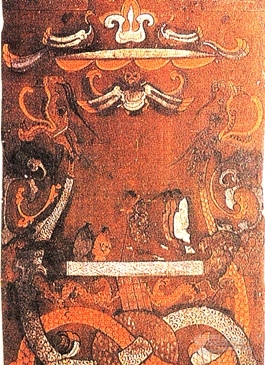
图4.4《汉代帛画升天图》局部
这幅帛画的主体人物是一位老年贵族女性,在向着天堂缓慢行进。在其周围的种种形象的描绘,都充满了神话及巫术世界的喻意和神秘的象征。这一神奇而浪漫的境界同时也是作为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而展现的,可以把这幅帛画视为浪漫型的工笔仕女画,也可以把这幅画看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洛神赋图》等理想性大于世俗性工笔仕女画的渊源之一。
此件作品绘画技巧处于初级阶段,并无更多的“规范”约束,体现了汉代绘画在形式技法上更具自然和天真之面目,也体现汉代艺术特点中没有受儒家狭隘功利信条的束缚的另一面,它通过神话、神、人等形象画面,展示了另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意志延伸的形象化,是人征服客观世界的意识体现,也是汉代艺术的重要观念,是“喷发式覆盖”为绘画表现方法的。
汉代国势强盛,有着“征服”天下之时代精神,其艺术同样除了自身面貌是大气度之外,所表现的内容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仿佛对一切都感兴趣,对一切都有着天然的热情。而文学由于可以任思维纵横驰骋,可以没有限制地描述和夸张更大更多的东西,无论天上地下都能置于笔下。汉赋正是这样,状貌写景,铺陈百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如:“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班固:《两都赋》)[2] 把情之所至的一切都尽性地描写出来,这和汉代雕塑、画像石、壁画等“喷发式的覆盖”之艺术精神是一致的,由于汉代尚无“雅”之理论引导或者说限制,绘画构图上,以“满”、“全”为主势,色彩上以“随类赋彩”的尽情涂抹为能事,它们以“征服”精神展示出了人的胜利和人的自信。尽管汉代美术属于中国绘画的初期阶段,有“粗重拙笨”的特点,但气度宏大而雄沉,敢于和善于作“正面描写”,而无一丝“取巧”之意,表现出的是具有“热”感的“画卷气”,因此具有作为中国绘画“典范性”开端的意义和价值。
[1] 参考李泽厚《美的历程》118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 同上131、132页
这种观念影响下的浓墨重彩绘画特别是这幅帛画工笔仕女画的形式,有着“解衣磐礴”任自然,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现实主义绘画观,是中国画“典范正大”之感的开端,对唐代“焕烂而求备”的工笔仕女画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4.3、春秋两汉时期有关仕女画的理论
春秋两汉代专门的艺术理论很少,大部分散见于各种书中,且仅有少数论著涉及到仕女画。《左传》的“使民知神奸”论:“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神奸”。“这段夏朝‘铸鼎象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作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代表理论。‘使民知神奸’,说的是育铜器图纹的社会作用。这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1] 虽然这一理论没有直接谈到仕女画,但是道出了仕女画作为绘画种类之一的共同之处,即社会作用,启示着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见”的绘画社会功用理论。
《淮南子》[2] 是一部涉及到仕女画理论的书,其中“君形”论和“谨毛而失貌”论对绘画产生的影响较大,并和仕女画有关:“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西施是古代的美人。孟贲是古代的勇士,据说他有生拔牛角之力。“君形”就是神,神似。君本为皇帝之意,这个词被借用来形容事物的主次关系,君形就是人的主神,再引申为神似。如果西施只是美但不使人欢喜,画勇士孟贲尽管眼瞪得大,却不使人产生畏惧之心,原因就在于没有画出他们的“神”,即各自特有的神态。据此,秦汉时期应该有“美”并“可悦”亦即更“女人味”的工笔仕女画,而不仅仅是宗教或政教范围内的仕女类绘画,虽然目前尚无此种绘画的考古发现。“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淮南子·说林训》)“古时,寻为八尺,常为一丈六”,是说在一般的距离之外,若过分地讲求作品的细节就会失掉整个作品的面貌,不能脱离整体而孤立的对待局部,工笔仕女画当然也是如此的。
《尚书》中有“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3]《礼记》中也有“天子之冕朱绿藻”的色彩之说,[4]《说文解字》更把色释为“颜气也”,而“颜”是“眉目之间也”,[5] 意为内心活动能反映在面部的色彩上。这就把色彩从主客观两方面结合起来看了。所以,汉代的绘画艺术虽然没有东晋顾恺之那种明确的传神等理论为指导,但却是较为自发地运用着传神和整体面貌以及色彩的理论,为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和谢赫的“六法论”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也为唐代工笔仕女画“焕烂而求备”的绚丽色彩打下了基础。
[1] “春秋两汉”分段和《左传》“铸鼎象物”之说,参考葛路先生《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春秋至两汉绘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2] 参见《四部丛刊初编·子部·淮南子》,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书
[3] 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五》,清 阮元 校刻,中华书局出版(重刻宋版注疏 影印本),1980年10月第1版
[4] 《十三经注疏》《礼记.礼器第十》,出处同上
[5] 见(汉)许 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181页
4.4 魏晋南北朝的工笔仕女画和绘画理论
《贞观公私画史》中记载的《洛神赋图》,《列女图》,《列女传仁智图》、《列女传贞节图》,《列女传仁智图》,《东图玄览》记载的《洛神赋图》,《宣和画谱》记载的《女史箴图》和《清河书画舫卷一》记载的《列女仁智图卷》等唐代以前的绘画,是工笔仕女画的起源之一,这些工笔仕女画的目的在鉴贤寓戒。
当时社会对于妇女的要求是重德,女性的举动均须纳入道德准绳。班昭的《女诫》说:“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浊,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麈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妇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也。”[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形象受此影响,在造型上多为“秀骨清像”,骨气为重。[2] 这也为谢赫“六法论”提出“骨法用笔”作了一定的铺垫。由于绘画本体的惯性及不平衡性,这期间见于《贞观公私画史》著录的仕女画如陆探微的《蔡姬荡舟图》、解倩的《丁贵人弹曲项琵琶图》、孙尚子的《美人诗意图》等已见出端倪近于唐代仕女画。其中谢赫的仕女画尤为突出,姚最在《续画品录》中说:“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眼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髻,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是没有一统天下的大国,更没有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思想上相对自由开放,由此带来人们意识上审美触觉的延伸。加上前代文化积淀和文化本身一定的惯性作用,使得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都由事物外部面貌的描绘进展到内部精神状态的刻画。绘画中尤其是工笔仕女画在形神的表现方面最为突出,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传图》等为印证。文人参与绘画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提高了绘画的地位,建立了“正雅”的审美标准;“传神”和“气韵生动”论为代表的绘画探索之思想结晶,使中国画由汉代生命意识自然迸发又融入了理性作用的导引,留下了《洛神赋图》为代表的一批传世之作,开启着唐代工笔仕女画既有“生命意识自然迸发”之热度,又有理性成分在内的“古代典范性”[4] 的绘画风貌。
[1] 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初版,1973年上海第二次印刷
[2] 见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周昉仕女画研究》第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
[3] (旧题陈)姚最《续画品》(津逮秘书本),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4] 单国强《古书画史论集》384页:张萱、周昉所创造的贵族妇女美的典型,被后世称为‘唐妆’。……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视为仕女画的典范,甚至认为树立了万世之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1年
4.4.1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
“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以形写神”必须参照着对象的形体、外在神情和内心情感进行绘画,而自己主观臆造,就不能“传”出所画对象的“神”。这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其理论著作《魏晋胜流画赞》[1] 中提出的著名现实主义绘画论观点,至今也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传图》等作品中体现出了“形神兼备”的特点,为后世绘画特别是唐代工笔仕女画提供了直观的楷模。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绘画在儒家为主的思想影响下,由“政教”推动而发展,也主要为“政教”服务。统治阶级对雕塑和绘画的态度决不是单纯为了欣赏,是利用艺术形式或歌功颂德宣扬自己,或为了祈求升仙得道。社会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受战乱等,但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能力也在逐步地发展着,因此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先秦以来的名、法、道诸家代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儒、道互补在这一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由于当时的战乱形成了许多个国家,没有了秦、汉那种大国的集权统一,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谁也管不着谁,因此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文学艺术领域里出现了许多历史上有名之人,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作“洛神赋”的曹植,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等等,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开启了艺术本体发展的新时期。这种艺术本体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思想和认识能力发展的体现。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主要是自身意识的增强,从神学和宿命论的屈从中解脱出来,重新审视自身,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人生追求。人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总在积累和发展,识人以“神”而不单是形。
重视“神”在这个时代,是与社会的进展相关联的。就连《文心雕龙》这样有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文艺理论专著都能在此时出现,那么包括工笔仕女画在内的人物画从重外形逐渐转到重内心之神,注重人的自身风貌即“形神”,进而“以形写神”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形成,就是必然的了,“传神论” 是由东晋时期的大画家顾恺之提出的,或者说是由他对前人的经验作了“水到渠成”又比较完整的理论概括。自此,“传神论”成为了中国人物画起点的、又是最高的标准要求,同时也是由汉代相对“自发性”的绘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觉性”绘画的成熟标志。
[1]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魏晋胜流画赞》:“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
文人参与绘画和文人审美标准的建立,是“自觉性”绘画的成熟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这一时期绘画风格的重要特征。一提到文人画,似乎多少有些轻松之意,马上就能和业余的、不求形似、逸笔草草的“笔墨游戏”联系起来;但此时的文人画和宋元的文人画有很大区别,如顾恺之本人即是文人也身居官职,但他的画无一丝一毫的“意笔草草”“不求形似”,[1] 而是努力地“以形写神”,力求做到“形神兼备”,绝无“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2] 之说。所以对文人画应历史地、分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与文人画相对的,恐怕就是画工画了。画工,由于是以画谋生的阶层,并且很大程度上要听从权势的任意支配,自然不敢“游戏”,更唯恐“不中绳墨”,怕丢掉饭碗。尽管画得熟练后可以发挥出“个性”,可以豪放,但终究放开的程度上,还是不能与不以画为生的官僚阶层相比。即便被画工称为祖师爷的吴道子,也还是大唐朝庭的官员“宁王友”,只有他才能“当其下笔风雨快,笔墨未到气已吞”、[3] “离披点划”、“一挥而就”。文人画与画工画虽在绘画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有两种面貌,当然也还是有雅俗之分的。
从劳动、生活创造了文化艺术的角度看,艺术一定要靠文化来不断地提升层次;而文化又要靠生活不断地补充新鲜营养,如同“雅”和“俗”一样,二者互为促进,缺一不可。这样,由于社会的发展,自由意识的积累递进,文人官僚们逐渐被图画的美所吸引,便开始了绘画的参与。由于文人权势们的介入,自然而然地提升了绘画的社会地位和本体层次,从春秋战国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 到魏晋南北朝谢赫的“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生沉”,[5] 到唐代张彦远的“与六籍同工,四时并运”,[6] 绘画的地位不断提升。六朝的梁元帝箫绎便是画家,《职贡图》传为其作,东晋,顾恺之、王羲之这两位大画家、大书家,是朝廷的大官;其它一些著名人士如稽康、阮籍等也都是文人名士。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人介入了绘画,一方面推动着绘画技法向前进展,如顾恺之创造了“高古游丝描”,另一方面促进着审美领域由形到神不断拓展;更重要的是,画工们数代人的经验积累,经过文人画家们的理论梳理,形成了“正雅”[7] 和“气韵生动”的审美标准。这样,加之形而上“传神”的审美要求,包括工笔仕女画在内的中国绘画,有了一整套的系统规范,在汉代中国画“正大热烈” 的起点上,铺好了使其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也使唐代工笔仕女画有了健强的生长基因。
[1] 元代倪云林《清閟阁集·答张藻书》,转引自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174页。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后文凡引此书略去出处
[2] 宋代《苏东坡集·前卷二十三集“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见同注2
[3] 宋代苏东坡《苏诗补注·卷四》,见同注2
[4] 见《论语·述而》
[5] 见谢赫《古画品录》
[6]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7]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中及二阎,皆纯重雅正……”。
4.4.2 “魏晋风度”和“以形写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精神——“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是和“以形写神”紧密联系的。了解了这一点,就会对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气韵生动”之论理解得更深刻一些,它们都是指人物画不仅要画出人的外在形态,还要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风度。《世说新语·巧艺》记: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画裴楷,认真地画其颊上的三根毛。原因在于,“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传神”要靠人的眼睛,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脸面部分也是“有识具”之处,即“传神”中“神明”的体现之处,至于身体其它部位的活动对于传神“无关于妙处”,只是从属的和次要的。也可以说,“魏晋风度”促成了“以形写神”论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战乱频起,各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异常残酷,上层贵族的人物许许多多被卷进政治漩涡,差不多“今天是座上客,明天是阶下囚”,命运朝夕不保。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如最具风度的稽康、写《女史箴》的张华、山水诗人谢灵运等,这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乱加罪名送上刑场的。因此在这种充满动荡、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因此,相当多的有识之士便收起“达则兼济天下”之志,转而“穷则独善其身”了。于是从谈论时政转到了人物的风度和形、神的品评,这样,既可以保身又能间接地宣泄内心悲愤压抑的情感,所以逐渐就形成了这种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和忧恐的“魏晋风度”。放浪潇洒的阮籍和超然世外的陶渊明是具“魏晋风度”较典型的人物。阮籍有表达痛苦哀伤的诗句:“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抒发着受迫害又不敢明说的情感也创造出了“慷慨任气”忧愤之美的表达形式;陶渊明因为“密网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乃逃禄而归耕”。(李泽厚《美学三书》10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逃离了政治漩涡的他们,把心思放在了自然景色与寻常的事物上,在自然事物和田园劳动中寻找无奈的乐趣,同时也就有心思去寻求一种更深沉、更具高度的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陶渊明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如同劳动后在地头拄锄休息时的回望所得,从而开拓出了自然冲和的审美新天地,人物画的审美范围也因此有很大的扩展。他们二人的艺术风格就是“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由魏晋风度所影响的人物形像特征也就自然地一望便知:痩削的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这正是魏晋时期美的最高标准。
4.4.3 “气”——中国画核心理论的形成
“文以气为主”(汉·曹丕《典论,论文》);兵家的《孙膑兵法》中也有延气、利气、厉气、断气、激气之说,[1] 可见“气”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基本范畴。在我国,自殷周到西汉原始生命观和“气”概念就已经成立,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气功强身图》,即说明在汉代“气”这一概念就已经研究的相当深入了。在殷周甲骨文、金文的资料中,它主要是指风和大地的运动。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齐物论》中有:“大块噫气,具名为风”和《广雅·释言》有“风,气也”的说法,认为风就是气。
但是“气”到底是什么,至今没有清楚的界定。概括而言,“气”是人的生命及自然物质运动的能量。[2] 在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之中,“气”开始以“浩然之气”等面貌出现,随着在道家中人对外物的反应和时令季节自然变化的关注,“气”这一概念在追求解释生命和自然现象的思考中,内涵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了自然哲学的概念。“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道”就是“可以为天下母”的混沌元气,万物都从这混沌元气中生成而来,这就形成了哲学上的万物生成论。这种万物生成论中的“气”,许多方面都有运用,如在古代的医方中,可以看到“肝气、脾气”这样的概念;文学也讲“气”,《宋书.谢灵运传》“以气质为体”,等等。
绘画艺术,在六朝时以“气韵生动”(谢赫《古画品录》)为绘画品鉴和创作的第一标准;唐代绘画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旨趣。“气韵生动”,是“气”的核心;阳刚之气,即孟子的“浩然之气”,是气韵生动的主气,辅以庄子的“逍遥之气”,(可视为介于阳刚和阴柔之间的中气)带动着阴柔之气浑化运行,产生出中国画特有的美。中国画有着“解衣磐礴”这种作画心态下产生的画面效果,也可以称之为画面的“画卷气”。[3] “气韵生动”和“画卷气”构成的“气”,统引中国画演绎着历史、现实与未来,也是唐代工笔仕女画“真气充沛”之内在蕴籍。
[1] (日)小野泽精一等著, 李庆 译《气的思想》1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此观点是本人参考(日)小野泽精一等著、李庆 译《气的思想》一书而提出的
[3] “画卷气”是本人观点
4.5 中国画创作与品鉴标准——“六法论”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形写神”论的出现,标志着“自觉性”中国画的开始,并规范和铺建了一条中国画的健康发展之路,那么谢赫的“六法论”就是这条路贯穿到底的方向标。“气韵生动”在谢赫以前人们是不自觉地运用着,在总结前人特别是顾恺之传神论的基础的上,南齐的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概括出了品评和指导绘画创作、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位的“六法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 [1] “六法论”出现后,一直是作为中国画创作、品鉴乃至学习的标准和美学原则,尽管后世的理论千变万化,始终没超出其范围。
“六法论”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涵盖了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创作和流传各方面。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2] “六法的提出具有绘画实践及理论探讨的总结性意义,对后来绘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 在“六法论”之“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运用方面,唐以前人物画“尚骨”,[4] 而唐代工笔仕女画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尚骨的同时又重肌,较为完美地演绎了由“骨法用笔”到“气韵生动”;并把汉代的“颜气”之主客观并重的色彩理论发扬光大。这些,我们在唐代工笔仕女画“丰颊肥体”、“焕烂求备”的大唐丽人的形象中已经感受到了。
4.5.1关于绘画中的“气韵”
虽然在论文方面早已有曹丕“文以气为主”,但把“气”纳入较为完整具体的绘画理论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出自谢赫的“六法论”之“气韵生动”。
有关“韵”字的解释,较早的在蔡邕《琴赋》中有“繁弦既抑、雅韵乃扬”之“韵”字,陶潜在《归田园居》诗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句,《世说新语.任诞》中也有“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之说,谓阮浑是阮籍的儿子,其风韵、风度像他的父亲一样。[5]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和韵是同时出现的概念,并为当时社会风气所追求和崇尚,对于人物清远、高雅、通达、放旷的气韵风度也就是“魏晋风度”最为崇尚,据说嵇康就是此种的风度之典型。这样,在人物画上也讲“魏晋风度”的表现,到后来逐渐把最初以体现“魏晋风度”的“气韵”纯化为人物画的本体追求了。
[1] “……虽画有六法,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賦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见(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津逮秘书本),于安澜 编《画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另参见黄宾虹、邓实 编《美术丛书》(共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的《古画品录》
[2] 参见郎绍君《中国画介绍》中国美术网,WWW.ARTCN.ORG2004年9月
[3] 见薄松年主编《中国美术史教程》80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4] 参见《滕固艺术文集·唐代式壁画略考》193页,沈宁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5] 参见阮璞《中国画史论辩》第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在绘画对人的表现中,以“气”为骨,“韵”为肉。“气”,必需有“韵”才成形;“韵”,也必有“气”来支撑。因此它们不能分开,合称为“气韵”。顾恺之的“传神”论重视眼睛和脸面的刻画,谢赫以“韵”的概念把“传神”之意扩充到全身乃至。“气韵”论后来由此扩大到花鸟、走兽、山水等各种绘画对象,五代山水画家荆浩在《笔法记》[1] 中就有“气、韵、思、景、笔、墨”的“六要”之说,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也说“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宋代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进一步把画的气韵与作者自身的人品相结合,有“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之论,宋代邓椿在《画继》中干脆讲“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
人物画上以人为载体来表现人的“神韵”,并以这种“神韵”来规范和引导“形”乃至形式技法上的变化,是包括工笔仕女画在内的人物画“道技并进”的重要开端,前面所谈到的顾恺之的工笔仕女画《洛神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4.6 儒、道、释思想观念与仕女形象塑造
中国传统绘画在实质上是哲学的具体化、形象化。[2] 工笔仕女画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独立性开始,区别于秦汉时期的最大特征,是仕女形象在具象表现上的意象性。这一时期的仕女形象除了写实因素[3] ,更多的是理想色彩浓厚的意象形象。例如,尽管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理论,和为裴楷画像时注意并强调“有识具”的“颊上三毛”,但我们看他的《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一个结合型以意象为主“秀骨清像”的形象,至于他的其它仕女画《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莫不如此。这种意象形象的思想内涵源于儒、道、释哲学。
意象在“美学的意义上增强文学的含量和艺术的张力”,“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意象实际上可以視为文化与心理的载体,以有限的物象形式负载着无限的意义内涵,从而构成其主要的价值和特征。而每一具体的意象几乎都具有各自的构成与渊源”。[4] 工笔仕女画就是这种具有着文化意义和哲学内涵的意象,也是文化与心理的一种载体。从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化思想氛围来看,在玄学思想氛围中,魏晋士人受言意之辨的影响,追求一种“神形超越”的境界,力求将自己的主观意味投射于客观事物上,借外物以寓情,以创造物我交融的意境。其中,对“蝉”的意象关照与仕女形象的产生有一定的内在类比,我们不妨参照一下。太康文人陆云《寒蝉赋序》云:“昔人称鸡有五德,而作者赋焉;至于寒蝉,才齐其美,独未之思,而莫斯述。夫头上有缨,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节,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
[1] (旧题唐)荆 浩《画山水赋·附:笔法记》,《四库全书·子部》1773年原文电子版,济南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研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参见林树中 王崇人主编《美术辞林.中国绘画卷·上》137页
[3] 这方面谢赫应是一个例子,姚最在《续画品录》中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需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精研,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装,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竟新”
[4] 参见《江海学刊》2000年第6期《意象的文化心理分析》栏目的“编者按”
该段序文把蝉归纳出了“文”、“清”、“廉”、“信”、“俭”五德,[1] 把士人理想人格在比附在蝉这个意象载体上,使其成为士人理想人格的符号象征。这种比附的思想源于儒家思想。孔子之后,有代表性的是思孟学派。思孟学派继承了孔子“内省之学”的精神,讲求“内圣外王”之道,遂成为后世儒家之正统。思孟学派重视内在心性的完善,要求锻造出一种理想的人格,去建立完美的社会价值秩序。在这一层面上,蝉被后世士人赋予的文化内涵正与儒家的人格要求有着奇特的同构性。蝉的“五德”之中,“文”是最重要的,即讲究仪容。儒家尚礼,仪容当然十分重要,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反映了儒家对形式美的要求。至于“清、廉、俭、信”意义相近,都是儒家对人格品行的要求。前面说过,仕女画的形象自顾恺之开始,由前代的具象性为主转到了意象性为主,几乎成为了一种象征。某种意义上说,同样是士人阶层创造的仕女画形象,和士人阶层把自身向往的理想比附于蝉的做法是一种“异质同构”的行为。然而,仕女画形象除了儒家“立德”、“尽美尽善”之内蕴外,更多的是道家的意蕴。老庄之道以无为作宗旨。道是无意识无目的、无私、无欲、无争,所以说道是无为。但道是生万物的,所以又是无不为的,“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反对儒家宣扬仁义礼乐等救世的有为态度,主张“守柔”来无为。老子说:“柔之胜刚,弱之胜强。”“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2] 老庄以柔静为美,他们塑造的人的柔静形象是婴儿,是处女,是真人。 老子说:“搏气致柔,能为婴儿乎?”意为聚精气以致柔顺,能像无欲的婴儿吗?老子形容婴儿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3] 孟子也德比赤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庄子幻想的神仙形象是柔且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4] “处子”般的神人,无疑是以女性为意象原型的。这种“神人”,亦即最能体现庄子的无为思想的真人。“庄子在《大宗师》中写道;‘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傈,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爱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真人没有喜怒哀乐恶憎之情,也没有利害得失之虑,生死置之度外,将万事万物等量齐观。孔子树大德大功的帝尧为精神美的楷模,庄子则立彻底无为至静的真人为精神美的榜样”。[5]
[1] 参见《蝉意象的生命体验》尚永亮 刘 磊《江海学刊》,2000年第6期
[2] 《老子·第七十八章》、《老子·第七十六章》
[3] 《老子·第十章》、《老子·第五十五章》
[4] 参见葛路、克地《中国艺术神韵》第5、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同注4
从上述论说中我们可以直接联想到儒道互补的顾恺之仕女画的哲学内蕴。在“赤子”之意象内蕴上儒道相通,在“文”和“守柔”的内蕴上也是同一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入世”和“出世”的精神性方面。而在“出世”、没有利害得失之虑方面,又同释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思想有了联系。更为相同的是,仕女画是儒、道、释思想都可以关照和透射的对应物、思想感情的载体。一方面,仕女形画象成为确证主体个性和人格的对象,另一方面,主体意念及其对现实的观照又借仕女画形象得以更深刻的显现。在仕女画意象中,除了悦目的美感外,既有士人画家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向往,又有对洁身自好、不合流污品行的赞誉和认同,同时也有人生失意和洞悉人生的感慨和生命依恋。正是这些,组合成了绘画作品中独特的工笔仕女画意象,并使其具有其它绘画形象意象所难以替代的独特意义。

图4.5 《洛神赋》(局部)
4.7 顾恺之的工笔仕女画
顾恺之(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今江苏无锡),义熙中为散骑常侍,博学多才,诗文书画皆能,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列女仁智传》等。顾恺之以《洛神赋》(图4.5)为代表的作品也是完整面貌工笔仕女画的开端之作,[1]这样他也是有作品流传下来的第一位工笔仕女画画家。尽管他流传下来的作品都被认为是摹本,但都应该是很接近原作的、并且是高手所临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的确体现了顾恺之所创“高古游丝描”“春蚕吐丝”、“紧劲连绵”的特点,表达了舒缓、高古而典雅之美。而且,就其“高古游丝”的线条来说,体现了“百炼刚化做绕指揉”、功力积累而至的典雅美,我认为这种美最充分地体现在《洛神赋》这一自由而浪漫的作品中了。在这幅以曹植描写他自己和洛水女神爱情故事的文学名篇《洛神赋》为脚本创作的《洛神赋图》画面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节:曹植路过洛水之滨,恍惚中看见了他所挚爱但无法得到的甄氏化身为洛神出现在河面上,人神隔水相望,默默无言;洛神为典型的魏晋美女“秀骨清象”,风姿气度高古而纤丽淑婉,轻盈修长,顾恺之把洛神与曹植相遇时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深沉细腻: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始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动势含蓄地“微波凌步”,“若往若还”,从而成功地昭示出了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晋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2] 也初步规范出了工笔仕女画含蓄超逸[3] 的审美特定标准。顾恺之以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高古游丝描”,成功地塑造了洛神形象,也成功地塑造出了曹植在岸边“呆若木鸡”的形象,使这一缠绵悱恻、凄婉悲凉的传世文学名篇之美深刻而形象化地展现出来,创造了具亦真亦幻、人神共处的凄美之境,为后世展示了这样的成功范例:生活上升到艺术,艺术手段的掌握是关键,它将感情化为理性的技法,随着情感表达之需要当放则放,当收则收,将迹化在画面上的线条色彩幻化还原成最初作画的那种感情。这就是工笔人物画尤其工笔仕女画艺术手段的高妙之处。《洛神赋图》共有四种摹本,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本文选用的是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摹本的图片,见于林树中《海外藏历代中国名画》。
[1] 见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周昉仕女画研究》第5页:“画谱亦云……列女傅仁图,外如顾恺之有洛神赋图卷,女史箴图卷,陆采微有姜后冕冠图。此都以妇女为表现题材,实为仕女画的起源。”
[2] 参见李湜《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美术网,www.artcn.org,2004年9月
[3] 参见林树中、王崇人主编《美术辞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170页:“高逸,指胸怀高远,意趣清脱,不受世俗常规定法束缚的画风。‘高逸’就是‘平淡天真’”。

图4.6 《洛神赋图》中洛神和曹植
顾恺之流传至今的作品《史箴图》、《列女仁智传图》也都各具特点,体现了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和“秀骨清像”的典型风貌。
《列女仁智传图》(图4.7),宋人摹本,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根据汉代刘向所著的《古列女传》人物故事而创作,内容是颂扬与标榜妇女的明智美德。此画所用较粗的“高古游丝描”,几乎类于“铁线描”,但和铁线描有所区别,线条凝重中依然见舒缓。在染法上将线与染痕分开一定距离,造成一种独特的平面效果。在“卫灵公与卫灵夫人”一段中,画卫灵公与夫人相悟对,两人内心情绪刻划有致,如对卫灵公形象的刻划,既流露出内心对夫人识别贤德的“仁智”感到惊讶,又不失自身矜持的身份。

图4.7 《列女仁智传图》

图4.8《女史箴图》局部

图4.9《北齐校书图》局部
《女史箴图》(图4.8),唐人摹本,绢本设色,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此画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一文所绘。张华原文歌颂古代具有贤德的宫廷“女史”(即女官),宣扬宫廷妇女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据传是为了讽谏放荡性妒、擅权祸国的贾皇后。[1] 全卷共12段,现存9段,每段后有“箴”文。存世9段的内容分別描写“冯媛当熊”、“班姬辞辇”、“修容饰性”、“同裘以疑”、“微占荣辱”、“专宠渎欢”、“靖恭白思”和“女史司箴”等。此长卷对人物神态的表达尤为重视,每个人的动态与情节都根据“箴文”内容创作,用色不是很多,暖色调,在线描上体现出了“春蚕吐丝”、“紧劲联绵”等特点。
4.8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的工笔仕女
唐代以前的绘画中北齐的杨子华有《北齐校书图》(图4.9)流传下来,尽管有人认为此图是初唐阎立本所画,更多意见是至少底本是杨子华所创。此图内容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命人校刊国家所收藏的五经诸史等书的故事。此画为绢本设色,里面的仕女形象和顾恺之作品中仕女的形象共同处在于“秀骨清像”,不同处在于更生动自然些,仕女的脸部运用“三白法”,即额头、鼻梁和下颏尖用白粉提染,这种技法是顾恺之作品所没有的。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杨子华“世祖时(按:武成帝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尝画马于壁,夜听蹄齧长鸣,如索水草。图龙于素,舒卷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入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见《北齐史》)阎立本云:自像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和《北齐校书图》中人物形象差不多的,还可以从北齐娄睿墓壁画人物形象(图4.10)上看到,虽是画的男像,长圆形脸较简单的发型与顾恺之作品中的形象有联系。这种特点也能从初唐壁画的舞蹈仕女形象(图4.11)上看到,舞女头部和发式与顾恺之、杨子华作品中的仕女形象几乎一致,只是在动作的舒展性、用笔的松快性上有不同之处,这些说明了仕女画发展的连贯性和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面貌及时代精神的展现。

图4.10《出行图》局部

图4.11《舞蹈仕女》
还有,梁武帝时期的大画家张僧繇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但他作天女宫女面短而艳[2] ,“上绍顾恺之陆探微,下启阎立本吴道玄”,如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载阎立本观张僧繇画“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之事,唐代张怀瓘《画断》中“吴生(道子)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吴道子“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的画风和张僧繇所创的“疏体”一致[3] ,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唐代工笔仕女画的影响。
[1] 刘人岛主编《中国传世人物名画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
[2] 见宋代米芾《画史》
[3] 参见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唐宋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